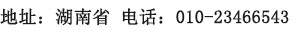谈到女性形象的描写,读者的固定思维都会出现“男性”,即女性形象的描写通常会与男性形象捆绑在一起,很少说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去完成一个故事,但是当男性作家去叙述两性关系时,与女性作家的叙述角度也会出现巨大差异。关于女性与男性的捆绑,在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中,这一差异性更为明显。两性关系是一个实在的命题,《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与蒋丽莉便是以强烈的自我选择性去阐述了这一命题。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有着典型的上海女人风情。她是闪耀的,有着绝对的美艳与聪慧,能在那一段苦痛的日子里活得从容不迫。她的故事,若是挑剔一下,按传统观念来讲就是缺一个能依靠终生的男人,否则就是完美的了。她有学识,是专属于女人的学识——她懂得如何表达,懂得如何穿衣打扮,懂得如何展现与保持自己的女性魅力。王琦瑶的风情不仅是在她的皮相,而是一种内放的风情,让人千般百般都拒绝不了,尤其在两性关系中,这明显体现出其主体性。在感情的选择上,王琦瑶的一生经过了六个男人:程先生、李主任、阿二、康明逊、萨沙和老克腊。关于这六个男人的描写,在王琦瑶表现的对比下,他们是稍弱的,性格中或怯懦逃避、或平凡中庸、或堕落自私。就算是两性关系似乎稍占上风的李主任,在我看来他的影像始终是模糊的。王琦瑶与这六人全都有爱,只是程度不同、性质不同,虽然有些感情经历看起来是荒诞的、是脆弱的,但都是王琦瑶自我选择下的结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王琦瑶的感情关系里,父母是缺席的,亲人是缺席的,永远不缺席的只有王琦瑶的内心,只有王琦瑶的自我选择。王琦瑶对于女儿薇薇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薇薇就是王琦瑶选择并负责的“产物”。王琦瑶关心薇薇,但从来不会刻意地去管制,这在于王琦瑶掌握了自我主体性。所以在她的观念里,她也同样赋予薇薇一个主体性。其实王琦瑶是看通透的了,也反映在她的日常的琐碎言语以及结尾处的那一幕长灯:有那么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王琦瑶眼中最后的景象是从客体的角度观看自己,不再仅仅是人生走马灯的场面,而更像是抽离了个体本身对自己的一种观看,将死者与鲜活的鸽群所形成的对比是极具冲击性的“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文章以人起笔,又以草木作为结局,我们所看见的是生命的延续,又一季的花草能够拉开帷幕,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王琦瑶的选择,我们作为读者、或是说彻底的旁观者,是不必一定要持否定态度的,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有所探讨和出离,王琦瑶自己的人生对她而言已经做好了足够的预设与准备,女性为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和个体的自由。王安忆描写的蒋丽莉,虽也是上海女人,却截然不同于王琦瑶的性格,唯一相同的,就是固执,那份“我选择我负责”的固执。在她的家庭里,她的母亲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姨太太,父亲也是很久才会回家一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蒋丽莉的被爱得太少。在文章前部分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蒋丽莉是自卑的,是不善于与人交往的,可是蒋丽莉却从来不说屈服于谁。学生时期她喜欢与王琦瑶交朋友,于是她是掏了一整颗心给了王琦瑶,虽然这其中不排除有一点点“虚荣心”的成分,但可以看到的是,她对于友情的选择,是负责到底的。虽然被爱得少,但蒋丽莉却是强烈地去爱别人。在两性关系中,她一生只爱程先生一个人,甚至因为程先生喜欢王琦瑶,她忍着心痛都去帮助、去照顾王琦瑶。在大多数读者看来,她是“痴”,是“蠢”,对于她的态度是不屑,是同情。但在我看来,也会有不少读者会因为她的真而喜欢她。蒋丽莉的选择还在于她对于革命的热忱,对于*的热忱。她选择了*,也一直在为入*而努力。投身了革命以后,蒋丽莉性格变了,变得外向,变得钢了,不再是那个只会写风花雪月的小女生了。但其实在她骨子里,还是当年那个蒋丽莉,还是那个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的蒋丽莉。蒋丽莉选择嫁给了平淡的丈夫,选择生下了三个她自己“嫌弃”的“一股臭脚丫子味”的儿子,对于这段感情,只能说她幸运在,丈夫和婆婆待她很好,尽管她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爱情,但把她的经历(除去癌症)放在现代社会,这样平平淡淡和和睦睦的家庭,是很多人都想要追求的。毋庸置疑的是,这段感情也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然而往更深层次看,她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只是身体上的妥协,精神上依然没有妥协。她精神上选择的是程先生,就算是精神上的负担,她也同样是为自己的感情所负责。“现代价值学理论十分重视生命感受对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