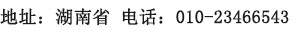回忆我的父亲文/张帅题记:父亲在世时不知有父亲节,我也从未给他买过礼物,过几天便是父亲节,再过一个月更是他的祭辰,特摘取几个与父亲有关的印象最深的片段记之,以此怀念我的父亲。(一)自行车我在大门前停住了脚步,望了望渐渐黑下来的天空,踌躇着不敢敲门。邻居家那条黄狗前几天因为咬了人而被铁链拴住了,没几天的功夫就开始眼睛发红、狂躁不安。大家都说它现在已经是一条疯狗了。此刻,它正透过邻居家低矮的院墙瞪视着我,身子一纵一纵,脖里的铁链哗哗作响。我缩了缩身子,努力不去看它的眼睛。一起下晚自习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回了家,夜色彻底笼罩下来。我还是不敢敲门,我怕母亲那双被贫穷和劳累折磨的黯淡无光的眼睛扫在我身上时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家里本就贫寒,父亲虽说在县城上班,挣的工资并不多,加上妹妹自出生后便一直体弱多病,日子经常捉襟见肘。母亲的娘家家境殷实,是外祖父母的掌上明珠。因为错信媒人的话,母亲嫁给了父亲。从小衣食无忧的母亲自从嫁进这个贫穷的家,便开始和父亲一起帮衬早寡的奶奶拉扯未成年的叔叔姑姑们,生活的巨大落差和无休无止的劳作让母亲的脾气逐渐变得暴戾易怒。她那些随时随地都可能升腾起的怒气无处发泄,就会全部撒到我和父亲身上,平时,我哪怕犯一点点小错,都会引来她的大发雷霆、暴跳如雷。父亲更是谨小慎微地陪着小心,生怕惹怒了母亲。一想到母亲那张几乎常年横眉立目、怒气腾腾的脸,我的心又缩了缩。天色越来越暗,大门边的草丛里蟋蟀的叫声也弱了下去。天地间的一切都在打着哈欠。我鼓起勇气拍了一下门,只一下,门就开了,门后是父亲的脸,好像他一直就守在门后,等着我拍门。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考试没考好?丢了东西?父亲观察着我的脸,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把自行车弄丢了!我终于没忍住,眼泪汹涌而下。“嘘”父亲把食指放在唇间,朝身后看了看。别让你妈听见了,你就说忘在学校了,知道吗?过个把月,我再到旧货市场给你买一辆一模一样的。父亲悄声说。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过的提心吊胆。可母亲还是从同学那里知道了我丢自行车的事,她一回到家,便随手抄起一把扫帚,劈头盖脸朝我打去,一边打一边骂道:你知道吗?你爸心疼你学校远,每天下班后就去路边给人家补车胎,整整补了一个月,攒钱给你买了那辆自行车,你倒好,一周不到就给弄丢了,你对得起他吗?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只任眼泪汩汩而下。旁边的父亲急得直搓手,暗示我讨饶或者逃走,我却不为所动。母亲打累了,扔了扫帚回屋躺下了。就像她以前无数次打完我之后那样。父亲拿来毛巾给我擦了擦脸,拢了拢我被母亲打散的头发,轻轻说:没事,爸再去补车胎,下个月再给你买一辆,下次,咱买辆新的。爸,我再也不骑自行车了,我以后走路上学。我把头倚在父亲肩上,抽噎道。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是走路上学,虽然为此我得比那些有自行车的同学早起半个小时,虽然,下了晚自习,我总是在夜幕沉沉时才回到家。走路上学三年,十五岁的我,个子竟窜到了一米六八,修长笔直的身材惹来同学羡慕。母亲调侃说是因为走路多的缘故,父亲却总是沉吟不语。好友小洁的哥哥从部队探亲回来,给她捎了辆白色的飞鸽自行车,和其他同学那些破破烂烂的车子比起来,简直就是鹤立鸡群。小洁爱惜的很,从不许别人碰它。哪怕我和她那么要好,她也只是让我摸摸。我想,我看小洁那辆白鸽的眼神一定落在了父亲眼里。上高中那年,父亲在单位转岗做业务,父亲勤奋敬业,业务做的很好,家境开始慢慢好转,母亲的脾气也随之温和许多。暑假里,父亲出差回来,我正躺在院里的竹床上午睡。阳光很刺眼,廊柱旁那株一人高的夹竹桃郁郁葱葱,刚好为我遮蔽出一片阴凉。父亲蹲在我面前,轻轻把我拍醒,我撩开眼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父亲的笑脸,他身后一辆崭新的粉红色自行车在太阳底下熠熠生辉。父亲给我扛回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二)红裙子家里有辆上海牌缝纫机,那是母亲的嫁妆。父母结婚时,外祖父知道父亲家底薄,特意给母亲备下了丰厚的嫁妆,一个大立柜和一台缝纫机是其中最值钱的,大姑姑结婚时,父亲背着母亲把大立柜当做嫁妆送去了姑父家。母亲知道后气得好几个月没搭理父亲。等到叔叔们长大成人要分家时,那架缝纫机就成了父母唯一的财产。从小到大,我和妹妹几乎没买过衣服,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用那台缝纫机裁剪出来的。母亲用她那双粗糙却不失灵巧的手,在缝纫机的“哒哒”声里,为一家人裁剪出四季衣衫。我和妹妹的小书包,也是母亲用做衣服的边角料做出来的。母亲会在我们的衣服领子上或前胸口别出心裁的缝一朵花或者一个小动物,让年幼的我们在一干小伙伴面前出尽了风头。直到上中学之前,我都穿母亲做的衣服。不只是我,周围的小伙伴们都穿做的衣服,也不觉得有什么。初中学校在镇上,班里同学大多来自镇上的双职工家庭。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和别人攀比穿着打扮,要比成绩,我铭记于心。可是,母亲和我都忘了一件事,我终究会长大,哪个少女不爱美呢?班里有个来自镇上的女生叫艾雨,父母都是医生,艾雨说自己有二十多条裙子,大部分是她父亲去大城市出差时捎回来的。每当她穿着那些时髦又漂亮的裙子走进教室,就会吸引所有男生的目光。包括我暗暗喜欢的那个男生。学校要举办运动会,需要挑一个女生在班级前面举牌子,一向喜欢我的班主任陈老师问我是否有红裙子,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条堂姐穿旧的白T恤和母亲给做的蓝裤子,窘迫地摇摇头,艾雨马上举手说自己有一条红色连衣裙。运动会那天,艾雨穿一条及膝的红色连衣裙,梳着高高的马尾,像一头骄傲的小鹿,举牌走在班级队伍最前面。学校先举行上学期表彰大会,邀请了受表彰学生的家长前来观看,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在第一排的父亲,我那春风满面、一脸自豪的父亲。上台领奖的我则沉浸在没有红裙子的羞愤里,没有接住父亲投来的目光。父亲疑惑不解。运动会开幕式开始了,艾雨举牌走在班级队伍最前面,她身上的红裙子像一团火,灼痛了我的眼睛。如果我有一条红裙子,那么此刻,站在队伍最前面举牌子的那个人就是我,可是,我没有。当队伍经过家长席时,我低垂着头,没有看父亲,只看着自己不断移动的脚尖,只觉得那条跑道前所未有的长。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是那么土气和难看,包括母亲为我剪的短发,也丑的要命。一种叫做自卑的东西悄悄钻进了我心里。周末回家,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急着和父母说学校里的事,只是沉默的写作业,父亲看着我,欲言又止。回学校时,父亲要送我,我拒绝了,自己搭车去了学校。中午很热,我在教室里看书,同学说楼下有人找我。是父亲,他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朝我挥手。打开包裹,一条红色的丝绸连衣裙倾泻而出,它简直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裙子,比艾雨那条红裙子不知要好看多少倍。这是爸去杭州出差给你买的,我闺女穿红裙子最好看!父亲含笑看着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运动会结束后,细心的父亲专门去找了班主任陈老师,陈老师顺便提了下红裙子的事,父亲便记在了心里。(三)羊角梳幼时,我的头发很少,不但少,还特别黄,和我的人一样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忙碌的母亲没空给我扎小辫,索性给我剪了短发。有了弟弟后,母亲更忙了,经常会忘记给我洗头发,我长了一头虱子,母亲有几次索性给我剃了光头,父亲实在看不下去,说一个小姑娘怎么可以剃光头呢?好歹不用剃光头了,父亲说他负责给我梳头发。他给我找来一把小姑姑用过的掉了一半齿子的梳子,开始每天帮我梳小辫。和大多数父亲不同,我的父亲心思缜密,情感细腻。他甚至为了我去请教邻居大婶梳小辫的花样。每每顶着父亲为我梳的小辫出门上学,我的心里都是美滋滋的。父亲甚至会用母亲做衣服用剩的布条挽出各种结,给我扎到头发上。我家院子里有棵桃树,弟弟出生时父亲亲手种下。来串门的邻居经常能看到我们父女俩坐在桃树下,我手里捧着本书,父亲手中握着我稀疏的头发,那双粗糙的手转瞬之间就在我头上捏出两个花骨朵来。一直到五年级,母亲说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学着自己梳小辫。可无论我怎么梳,总觉得没有父亲为我梳的好。中学最后一年,为了节省时间学习,父母决定让我住校。父亲让我坐在自行车前头的横梁上,把两大包行李捆扎在后座。一路上,他费力地踩着脚蹬子,摇摇晃晃把我送到了学校。铺好床,归置好个人用品,父亲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精致的羊角梳来,我摸着它晶莹剔透的身子,心中欢喜极了,这可是第一把专属于我一个人的梳子。我再也不需要用姑姑们用剩下的梳子了,不是断齿就是掉把,梳起头发来扯的头皮疼。父亲说,你长大了,是大姑娘了,必须得有个像样的梳子,也扎城里姑娘那样的马尾,那才好看。我送父亲到学校门口,看父亲骑车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后来,我到了更远的地方求学、工作,用过塑料梳子、桃木梳子,甚至名贵的檀木梳。却始终感觉没有父亲送我的那把羊角梳好用。那把羊角梳一直伴随着我,就如同父亲陪伴在我身边,让我安心。作者简介:张帅,女,河南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文学与写作。愿,以文字为媒介,结识天下文友,阅尽天下美文,乃,我心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