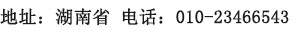作者张梦阳
一个人,从小心仪什么样的人物,长大就可能按照这个人物的模式塑造自己.这就是: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父亲和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临清的同乡,都是依靠山东省和清平县的奖学金上的大学.季先生上的是清华大学,学的是文科;我父亲张清濯上的是北洋大学,师从茅以升先生学土木工程,后来成为北京市*局的老高工,桥梁道路专家.回头看来,当时清平县的这一奖学制度是非常英明的.那时获奖学金的大多是穷困子弟,有了上学的机会都会发愤苦学.他们有一家个共同的特点:学业精进,生活朴素.所以,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英才,大学的副校长就出了好几位.当然,其中最为突出、最受敬重的是季羡林先生.
我小的时候,父亲就不断跟我讲述季先生刻苦学习、成绩超拔的故事,激励我以他为榜样发愤读书:“你季伯父啊,中学的时候,英文就很好了.据说他还能用英文写小说.”“你季伯父啊,很年轻就在报纸上发表很美的散文了!在清华上学时,就已经是名学生了!后来到德国留学,学习梵文,又精通英、德等多国外语.但他学问越大,为人越谦和,对老乡尤其好.从来不摆教授架子,像我们桥梁工地上的师傅一样朴实.越是这样,声誉越高!”在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做季伯父那样的人、那样的学者,成为我从小的志愿.
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二中读书时,季先生的散文一在报纸上发表,我就如饥似渴地捧读.我的启蒙老师、 散文家韩少华,在星期文学讲座上带我们精细地赏析过季先生的夹竹桃.
1964年上北师大中文系时,恰逢“左”风盛行.我也因拼命读书、写作而挨批,有些“左”得可爱的同学批判我说:“你之所以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思想根深蒂固,就在于你接触的人和心仪的人,全是些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也歪打正着,我心仪的人,确实是季羡林先生那样的高级文化名人,但他们确实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1973年9月中旬的星期一上午,我冒着晚回任教的农村中学会挨批评的风险,毅然和父亲、盛紫舟伯父一起前往北大拜谒心仪已久的季先生.先生给我的 印象就是:这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清癯老人,哪里是什么“资产阶级”,完全是一位极其朴实的老农民,很像我任教中学附近村里的那位菜园“老把式”,质朴得犹如菜园边的一块极普通的石头,却能将园里的瓜果蔬菜侍弄得琳琅满目,井井有条.后来听说北大新生把季先生当成老师傅,让他代看行李;等到迎新大会开始了,往主席台上一望,才知那位老师傅竟是副校长.有人听了不大相信,认为不过是传言.我听了却当即认定是事实.因为我 次见他时,如果不是在他家里,也可能误认他是老师傅.
他中午一回家,听说老乡来了,即刻惊喜非常,向我们热情招呼,在小厨房的圆桌旁坐下.他听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自小就喜欢他的散文,还听我背诵了夹竹桃的开头两句:“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就一下子兴奋起来,挤到我身边的圆凳上坐下,忙问:“李长之现在怎么样了?”
从中听出他虽然自己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还没有完全解放,却一心惦记着别人,尤其是山东老乡.
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耿介和睿智.当我天真地以为聂元梓下台形势就好了时,季伯父转为严肃,抬起右手,指指上面正色道:“问题并没有解决,她的后台还在台上呢!”
他的婶母和老伴担心他又会因直言惹祸,摆手不让他讲,他的犟劲却更冲了,挺直脖子,精神矍铄地说:“没关系的,都是老乡,自己人,不怕的.”
我那时才见到了真正的季羡林先生!
多少年了,季先生耿直的样子始终如在目前.以后我写了“文革”中,季羡林先生的一次家宴,发表在2003年12月3日中华读书报家园上,2004年1月9日作家文摘转载,以后又有多家报刊刊载,后收入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望大家里.
自见到季羡林先生的真人后,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为高大、具体了,激励我在农村中学的艰苦环境中,咬紧牙关,坚持读书和写作.
后来我收到过季先生多封来信,还见过他多次.
记得一次是1978年的一天中午,他下班后,顾不上午休,就伏在桌案前,在一厚叠稿纸上写作.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在翻译印度的诗.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巨著罗摩衍那.
再一次是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同学去看他.他正在房前的荷花池畔散步,见我们来了,立刻请进屋里.这时,他已对我的学习和写作情况有所了解,对我的同学说:“我很赞成梦阳的精神,许多人分到下面就颓废了,不学习,应付工作就算了,梦阳还坚持研究鲁迅,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有志气!不平庸!”
1979年10月,我终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趁到北大王瑶先生家取稿的机会,又去看他,告诉他新的单位.他说:“我知道这件事的.你干这件工作,正合适.调得对!”
1984年散文世界创刊,林非先生让我向季先生约稿.我又去北大东语系他的办公室找他谈了一个上午.季先生踔厉风发,指点江山.后来形成了访谈记季羡林畅谈世界散文.
1988年秋天,我正在文学研究所楼道里走,忽然所里一位美学家追上我说:“前天到季羡林先生家去,季先生托我问你好!”我心中一暖,忙说:“谢谢!谢谢!”美学家又问我怎么跟季先生这样熟悉,我告诉他:父亲和季先生是山东临清同乡.
1996年11月6日,我父亲去世了.我写信告诉了季伯父,两天后接到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的电话,说:“季先生很难过.想去看你,但年老不方便,你来一下吧!”
于是第二天傍晚,我去了季伯父家.他叹息道:“又走了一位老乡、老朋友.”悲情自心中涌起.我反倒劝他,拿出刚刚出版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赠他,他抚着书说:“比以前长进了!”很是欣慰,于是和我合影留念,后来陕西教育出版社的同志来京,要求我带他们去看望季先生.已经来不及事前打招呼,我只得赶紧写了封快信说明情况.第二天下午,到季先生家门口,李玉洁女士正在等候,我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没有征得季先生同意就来了.”李玉洁笑笑说:“刚接到信.这回是破例了,往常的客人都是得到回音才来的.我跟季先生说,张梦阳要来,你能挡吗?他笑着摇摇头,我就在此迎候了.”我们进去,我直向季先生致歉.他摆摆手,意思是没关系,就热情接待来访者,大家无不深深感动.
季先生住院以后,我极想去探视,但又恐打扰,只在写出“文革”中,季羡林先生的一次家宴一文后,给他挂号寄去,并问候.但我一直心仪着季先生,他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季先生研究梵文的那种“韧”性、坚实的“沉潜”精神鞭策着我,督促着我:历时九年主持编纂五卷一分册1000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翻译了鲁迅力主国人镜鉴的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写完了三卷本187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接着写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三部曲,立志像季先生那样写作到人生的 一刻。
写到这里,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称呼季羡林先生才最为合适?“国学大师”吗?“国宝”吗?明明季羡林先生生前一再“辞大师”“辞国宝”,为什么要硬加上这些他本人不愿意接受的头衔呢?他如果复活,一定要抗议的.而我在前文所说的“老农民”“老师傅”“老把式”等,也只是一种外貌的形容,并不能概括他的本质.他是一位像“老农民”“老师傅”“老把式”一样的劳动者,但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精神领域的劳动者.最恰切的称谓,我想应是“精神劳动者”,一位世上少有的勤恳、深邃、韧长、博大的“精神劳动者”.倘若季先生活着,还能和他谈心的话,我以为他会接受这一称谓.
哲人已逝,精神长存.我永远心仪着季羡林先生.
———2009年7月12日下午16时,冒酷暑到北大季羡林先生灵堂吊唁,缅怀往事,不胜悲痛,季伯父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构思心仪一文,回家写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