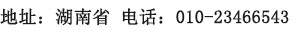千枝光照海,
龙船花发四眉啼。
龙舟花丨
过了端午,正是龙舟花开得最盛的时候。
小区临水的凉亭两侧,龙舟花花团锦簇。午后下了一场暴雨,经雨的花瓣,细细碎碎的,显得格外干净,神气。
龙舟花未开时,很像一根根微形的细簪。待到开放之后,四片花瓣平展成一个个小十字,又像一颗颗骄傲的小星星。无数个小星星凑在一块,犹如一团橙红色的绣球。
但龙舟花怎么会是绣球呢?
它是茜草科、龙船花属植物,而绣球花是虎耳草科绣球属的植物,它与绣球之间,连表亲都算不上。
南方的雨季,叫“龙舟水”。一直怀疑龙舟花的名字,与此有关。
福州人叫龙舟花为山丹。山丹的“丹”字,大概是指它的颜色吧。龙舟花的花色丰富,有红、橙、*、白、双色等。但我在福州,见到的都以红、橙双色为主。
叫它山丹,很是贴切。
龙舟花原产于中国南部及南亚。这是一种典型的南方花卉,连《本草纲目》都鲜有记载。我国人工栽培龙船花大概在十六世纪,我能找到写龙船花的诗词,只有清朝的两位南方文人。
一位是清乾隆年间,主讲福州鳌峰书院达十一年之久、建宁人朱仕玠的《瀛涯渔唱》:“柴门五月满蓬藜,闲把光风细品题。 千枝光照海,龙船花发四眉啼。”
另一位是清末台湾举子陈肇兴的《端阳》。“几家桃李荐新鲜,艾叶榕枝处处悬……记得水仙宫畔里,龙船花外放龙船。”
日本人称山丹为“三丹花”,或者“三段花”。
这是因为龙舟花每年可以分三次盛开,春夏秋冬,都有它碎碎的花影。山丹的花还可以入药,治月经不调,闭经,高血压。
山丹说,我不要月经不调,我不要高血压。其实它一点都不想入药,只想安安静静做它的山丹,开它的花。
夹竹桃丨
门口小公园里,夹竹桃已经繁花满树了。
夹竹桃是夹竹桃科夹竹桃属高大灌木,它的原产地,在南亚的印度,以及中亚的伊朗。大约在唐朝,自印度传入我国。
很少有人知道,当初引进这种竹不像竹、桃不像桃的灌木,并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提取它身上的*素,用于杀虫灭鼠。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六种*物常被提及,它们是断肠草、鸩酒、鹤顶红(砒霜)、夹竹桃、见血封喉、曼陀罗。
小时候,见过耕田的老牛误食夹竹桃,口吐白沫,立扑。牛主人强行喂食了一篮子的无花果,那老牛才晃晃悠悠活了过来。长长的牛脸上,一副怕怕的表情。
唐朝时,夹竹桃也不叫夹竹桃,而是用印度的译名。
夹竹桃的叶子似竹叶,细长纤巧,青翠欲滴,而花朵似桃花,层层叠叠,夏秋两季长盛不凋。宋人爱极了这种姿态潇洒,花色艳丽的尤物,便给它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叫夹竹桃。
北宋诗人曹组,称赞它具有岁寒三友一样的高风亮节。
“晓栏红翠净交阴,风触芳葩笑不任。既有柔情慕高节,即宜同抱岁寒心”。
而到了清末民初文人赵熙的笔下,画风突变,夹竹桃又成了赵熙想象中搔首弄姿的风情女子:
“非竹非桃。甚眉舒翠玉,泪掩红绡。新妆明灼灼,嫩叶影萧萧。天台仙子降湘皋。泪痕酒痕,春情未消。”
这贼贼的花花肠子,其实早就被夹竹桃看透。去你妹的赵熙,去你妹的泪痕酒痕,春情未消。有胆你放马过来,消一消试试?
茉莉丨
阳台上一盆茉莉开花了。灿若莲花般的花瓣,层层分开,润如白玉,薄如细娟。
茉莉古称“苜莉”,为木犀科、素馨属直立或攀援灌木。其原产地,也在印度,西汉时传入中国。
福州是茉莉之城。据南宋福州人郑域《郑松窗诗话》的讲法,茉莉是在汉代随同佛教传入东南佛国——福州的。福州人至今仍叫它“苜莉”,种“苜莉”,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福州的夏季,气候湿热、光照充足,土质疏松且肥沃,最适合茉莉生长。
北宋时的福州,已是中国的茉莉花之都。宋朝张邦基的《闽广茉莉说》说:“闽广多异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为众花之冠。”
福州的茉莉花茶十分有名,只要轻啜一口,便觉清香扑鼻,它是慈禧太后的 。
茉莉入茶,也在宋代。从宋代开始,福州人就开始制作茉莉花茶、茉莉花酒、茉莉花香水。《全芳备祖》记载:“或以熏茶及烹茶,尤香。”
在福州话中,“苜莉”寓意着“莫离”。送君茉莉,请君莫离。
冰心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苜莉是四海为家的福州人美丽的乡愁。那花香里,有福州人“莫离”的故乡情。
看到茉莉,便会想起电影《路边野餐》。老男人陈升坐了九年牢,出狱时,妻子张夕已离世。当他坐上那趟回家的绿皮火车,想起了张夕。
张夕以前很想听陈升唱歌。笨笨的他唯独学了一首《小茉莉》。
这个混过社会、蹲过牢狱的老男人,用颤抖沧桑的声音,老泪纵横地唱起张夕教他的《小茉莉》。
茉莉如心,爱妻莫离。但此时的张夕,已经听不到了他的歌声了。
白兰花丨
午后的暴雨,来去匆匆。
又一次听到子规的啼声了。暴雨之后的子规声急促而且凄厉。一棵白兰树,在子规声中落了一地的花瓣,让我想到来到这个城市时,那个白兰花瓣纷飞的夏天。
我在福州的 个落脚点,是中山路23号大院。
大院所在的冶山,在屏山东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年),闽越王无诸在此筑城建都,是福建省历史上 个城郭。明清时,大院是曾经的贡院。
这一落,就是十年。
那时的大院里,有成片高大的樟树林、白兰树林。
福州的白兰花,形体细长纤弱,白中略带着淡淡的*,质感细腻,小小的个儿,一副拘谨的初绽模样。花形虽小,可特别的香。夏日的轻风吹过,花瓣像雨一般地落下,清香扑鼻,让人忘却了林外的暑热。
每天清晨,有摘花人推着自行车,带着竹梯,来到大院里摘花。他摘花的工具,是一杆长长的竹篙,细的那头用铁线绑着一个小网兜,自行车的后座,还压着一个大大的网兜。
摘花人忙碌了一个上午,日午时带着一大网兜的白兰花,走了。
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摘花,每天摘这么多的白兰花,做什么用呢?
他们是收购白兰花的贩子。那些新鲜的花儿,他们会卖给香水厂,制造香水,或者卖给茶厂,薰茶用的。
向晚时分,福州的旧夏里,经常会看到买花女孩纤细的身影。“玉兰花(福州人叫白兰花为白玉兰)——苜莉花——”,卖花女孩在大街小巷一路穿行,一路叫卖。一声声略带稚嫩的叫卖声,在日复一日的市井岁月中闲散。
而曾经遇见过的那些花,在我心中却活了下来,活成一个个特别不舍的故事。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